民间文化:“了不起的海洋,了不得的宝库”
李勇
《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14日 13版)

陕北民间说书人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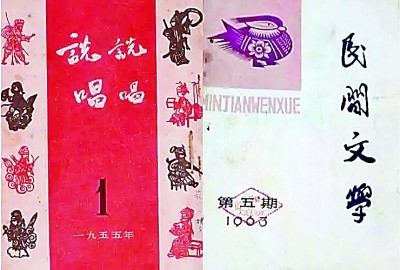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汪曾祺曾先后就职《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杂志,受到中国民间文化的深厚滋养。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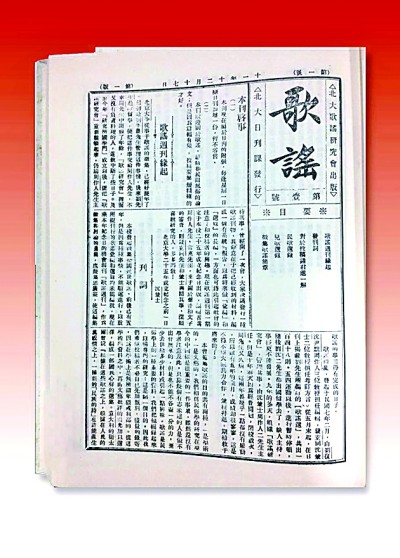
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由北大发起的歌谣运动,掀起了“到民间去”的民俗学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资料图片
一
近读河南作家冯杰的旧作《非尔雅》,感触良多。这是一部以乡村风物为“名”,加以“释义”的书。其中一节,释的是“灰脚”:“相邻两家的田地边界处、房屋边界处,仅仅以树、以篱、以墙为界,那是表面明处的,还有一种地下的证据,像暗处的力量。如果双方有争议,随时会出示有分量的证据。”读到这段时,恍惚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故乡,在我老家那个小院的东北角,便是灰脚埋处,彼时邻家盖房,地界有争议,我便亲眼见它被作为“有分量的证据”加以“出示”过。那是若干年前便立下的“契约”——“双方商议后,找一两位当事人,在规定处用铁棍探下一个两三米深的眼孔,续进眼孔里足量的白石灰粉,就叫灰脚。”据记载,石灰在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已被用于建筑,中国也在公元前7世纪开始使用石灰。石灰是显眼之物,亦能下药治病,“性至烈,人以度酒饮之,则腹痛下痢。疗金疮亦甚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都记载过它的不凡。但这个不凡之物易得,遂被用入了日常生活。然而,作为“灰脚”的它,关涉一个家庭的领土和主权,仍是不凡的。
冯杰的书写得有趣。毛驴腿上有“夜眼”,走夜路不迷;猪后颈味最美,遂成“禁脔”;布谷鸟乡下小名叫“光棍背锄”,鹅卵石被唤作“老鸹枕头”;人在鹅眼里会变小,在牛眼里却会变大——故前者有攻击性,后者温良恭顺……这些乡土“知识”虚虚实实,将人带回到久违的乡村生活。河南作家擅长写乡土。但这种书写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乡村生活的复原。在乔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宝水》里,百岁老人去世时,年长的执事一嗓子喊出的是“老太太宝婺星沉,福寿全归”,之后对那场古老葬礼的描写占据了惊人的篇幅。这描写显然是非现实的,因为除非是刻意的表演和设计,现在的中国乡村已很难见到这般古老庄重的传统葬礼。当然,恰恰是这种“非现实”性,展现出了作家执拗的情感和态度。
但更值得深思的,并不是这种情感和态度,而是在它的作用和驱使下,作家有意无意地俯身民间,挖掘和汲取本土文化资源的姿态。因为在一段时期内,很多当代作家并不这样做。王小波有篇名文叫《我的师承》,他是把查良铮、王道乾这些翻译家追认为自己创作上的导师。虽然通过他们,他也肯定了现代汉语对他的影响,但他所提及的《青铜骑士》《情人》这些西方作家的作品,其内容显然更是王小波灵感的重要来源。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文学和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特殊时代环境和文化氛围也造成了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某种迷信与执念。不久前,重翻马原的《小说密码》(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发现他在探析“小说密码”的举例里,竟罕有提及西方作家之外的名字。在某个大概不到二十页的篇章里,被提到的就有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普鲁斯特、纪德、海明威、罗伯-格里耶、萨洛特、梅勒、托尔斯泰、毛姆、乔伊斯、博尔赫斯……另一位当代作家王安忆谈创作的《小说课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倒是有不少章节专论中国作家作品(包括当代作家作品),但开首两篇长长的最重头文章,精谈细讲的却是《悲惨世界》和《战争与和平》。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对马原和王安忆有何微词,更不是说被他们举例的这些西方作家不优秀,而是说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能看出当年的文学乃至文化空气。近年来,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被强调,作家不再开口“三斯”(马尔克斯、乔伊斯、博尔赫斯),闭口“三卡”(卡夫卡、卡佛、卡尔维诺),但在民族文化资源的发现和发掘方面仍有一定盲区。
二
读冯杰的同时,还读到另一位已故的河南作家孙方友,他是豫东淮阳人氏,生前以“笔记小说”闻名,有《陈州笔记》(四卷)、《小镇人物》(四卷)传世。我极惊讶于孙方友笔下民间生活的丰富多彩,但和冯杰一样,孙方友在文坛的声名并不昭彰。这里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师承”——广袤的中国大地民间文化。冯杰、孙方友都来自乡土,没什么学历,创作除了靠天分悟性,就是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民间知识。这种“知识”不在书本和课堂,而是存身于星光下的桥头和麦场,大道旁的绿荫与茶肆,是于乡村生活的闲暇与缝隙里生长出来,以一种貌似可有可无、实则缺之不可的精神生活方式存在着。孙方友生前曾长久奔波于老家淮阳收集民间故事和传说,冯杰大概在做信贷员时便嗜读《酉阳杂俎》《癸辛杂识》《夜航船》。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里,确实有一种不为文人雅士所喜,也不见于经典典籍,甚至不见于文字记载,而只流传于口头的文化——民间文化。“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冯梦龙在《山歌序》中的这段话,道出了民间文化的“民间”性质——在古代,它曾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的一种文化。但实际上植根于广袤的乡野和大地,与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距离的民间文化,其自身一直充盈着丰沛的活力。大概从明末开始,民间文化的价值被一些有远见的读书人所重视,明清时期的冯梦龙、屈大均、王士祯、黄遵宪等在整理民间文学和文化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他们之所以重视对民间文学和文化的整理,极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它有着正统文人文学和文化所难有的真挚、淳朴、自然。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原因也无他——“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
明清之后,民间文化的价值日显。但其实这种千百年来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文化,其价值也并没有完全被忽视。居庙堂者要“观风俗,知得失”,所以一直有遣“采诗之官”收集民声的传统——“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至于文坛,有识有志之士或流落乡野的落魄文人,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山野之声涤荡诗文。就如鲁迅所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这些对待民间文化不无功利的态度,一直没有让这种文化的身影脱离正统知识分子的视线。所以,明清之际民间文化的振起之声,并非无迹可寻。当然,近古以来市井文化的发展和发达可能是一个更大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唐宋以来整个中国通俗文艺和文化的发展其实都可以纳入进来,从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到民国通俗文艺,这些都与民间文化千百年来的发展息息相关。“通俗”和“民间”并非同样的概念,但“通俗性”显然是民间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五四”之后以启蒙和革命为职志的中国知识界,才发出了“到民间去”的呼声。
三
1918年2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主持设立了一个歌谣征集处,他们在当时的北大校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面向全国征集歌谣,数月后又辟出“歌谣选”专栏,日登歌谣一则(前后刊出148则)。两年后,由沈兼士、周作人担任主任的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至此,由北大发起的这场歌谣运动,掀起了现代中国“到民间去”的民俗学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虽受时局影响,这场运动的中心在1927年之后移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但直到抗战爆发,这场民俗学运动持续给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强烈冲击。后来决定整个中国前途命运的左翼思想和文化,和这场文化运动之间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民间”始终是其最重要的文化支撑点和立足点。
在民间文化拥护者眼里,民间文化是一个有着自身历史、审美特性、独立而完整的主体性的文化系统。但对于民间文化来说,口头性、变异性本就是它的“基本特征”(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它和精英文化的互渗互融,更是古往今来文化史上的常态。所以,民间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是否存在,有无建立之可能,都值得商榷。然而有一点却是无异议的,那就是它确实有着实实在在的存在形式和历史,在漫长的民族生活中滋润过枯燥的岁月和时光。这岁月和时光又酿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文化记忆。在我年少时,最快乐的事情是去姥姥家,而去姥姥家最难忘的,就是跟姥姥听说书。说书者一般是在两个时节摆场子:秋后和年关——均是农闲,农民有余粮、舍得花钱的时节。常是在晚饭之后,姥姥拿着马扎,牵着我的手,到村子最开阔的所在——十字街头。那里闹哄哄已坐满了人,唠嗑的、嗑瓜子儿的、嬉笑打闹的……等唱大鼓的演员清咳一声,再咚锵一声鼓响,大家便安静了。那时我不喜欢听书,却也记住了《三侠五义》《杨家将》《呼家将》《封神演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等书名。印象更深的是主角登场前,总有个年轻徒弟先暖场,扮个老太太,唱个顺口溜,或变个小戏法,逗大家笑。主角登台后说的,是姥姥喜欢听的段落,她给我买一块江米糖,再买一块江米糖,我就能陪她到散场。
儿时听说书是难忘的乡村记忆,生于河南南阳唐河祁仪镇的作家李季(原名李振鹏)少时也有类似的迷恋:
振鹏特别迷恋鼓儿词和曲子戏。鼓儿词源于唐代的道情、道曲。清中叶,南阳的艺人将当地的民间小调糅入其中形成了“南阳大鼓书”。左手持月牙形犁铧翅,右手敲击八寸鼓,艺人手、眼、身、法、步相互协调,在打板和《长流水》《紧急风》《蜻蜓点水》《凤凰三点头》的或疾或徐、或重或轻的鼓点伴奏中吟唱。……唐河县城有个曲子戏班,来镇上演出时振鹏几乎场场去蹭戏,《施公案》《小八义》《薛刚反唐》,他看得眼睛都不眨。
“左手持月牙形犁铧翅,右手敲击八寸鼓”——这符合我儿时听书的记忆。但鼓儿词和曲子戏是南阳地方曲艺,我那时听的是“鼓书”——那是鲁北老家的叫法,其实就是发源于河北、流行于京津乃至整个华北的京韵大鼓。跟姥姥听书,我没有提起真正的兴趣,后来却迷上了收音机里的评书,那时已上小学,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袁阔成各具声色的嗓音,陪伴了我童年的寂寞时光。李季是听着鼓儿词和曲子戏长大的,后来追随革命队伍去了遥远的定边,在那里他迷上了顺天游(又称信天游),跟着当地的民间艺人、老农、盐贩,他边听、边唱、边记,后来就有了那本珍贵的《顺天游》,也才有了他将顺天游与现代诗嫁接改造而写成的名诗——《王贵与李香香》。
四
由民间文学提炼升华而成文学经典的案例,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屈原流放沅湘,“窜伏其域,忧怀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辞章句》)。也就是说,《九歌》乃屈原改造民间祭祀之曲的结果。而从《诗经》《史记》到六朝乐府民歌,从唐传奇到元杂剧,从“三言二拍”到“四大奇书”,再到《聊斋志异》《红楼梦》,莫不是由民间起步,经文人加工点化,一步步成为经典的。
谈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滋养,不能不提一个人:汪曾祺。“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京剧《沙家浜》“智斗”的经典唱段出自汪曾祺。这是汪曾祺语言魅力的一个缩影。这种魅力来自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也来自民间文化。了解汪曾祺者都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有过大概10年的创作早期,那时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派”,大多数小说都是意识流式的。他后来走向成功是在20世纪80年代。80年代的汪曾祺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充满人间烟火气和民间声色的汪曾祺。但一个“现代派”的汪曾祺究竟是怎么变成后来的汪曾祺的?这里面原因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应该就是他和民间文化的接触。这种接触在他小时候便开始了,但真正深入接触和了解,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汪曾祺在《说说唱唱》杂志工作,这本杂志创刊于1950年,由赵树理任副主编,汪曾祺任编辑部主任。汪曾祺后来撰文称赞赵树理是“农村才子”,说他“有时赶集,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口念锣鼓,拉过门,走身段,夹白带做还误不了唱”(《才子赵树理》)。《说说唱唱》停刊后,汪曾祺又进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下的《民间文学》杂志任编委,直到1961年调入北京京剧团。
也就是说,从1950年到1960年,汪曾祺有整整10年是专门从事与民间文学直接相关的工作——和民间文学作者打交道,参与整理民间传说,深入生活调查等。这些工作激发了他切实的兴趣,《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古代民歌杂说》等,是他出于职业需要但更是出于兴趣而写的研究文章。后来终其一生,他对民间文学都予以盛赞——称它“是个了不起的海洋,了不得的宝库”(《文学语言杂谈》),“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不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我和民间文学》)。汪曾祺的创作受民间文学和文化影响,很多人都曾谈到过、分析过,在此不赘述。想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直接带来了他创作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的汪曾祺在60年代初才重新提笔,发表了《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王全》、《看水》。这几篇小说取材于作家50年代的下乡经历,里面那淳朴的少年、劳动的场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及返璞归真的语言,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与40年代截然不同的、洋溢着平民化和民间化立场的优秀小说家。
在20年后的新时期文坛,汪曾祺能写出《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那些充盈着民间温情和烟火气的经典之作,是不让人奇怪的。正是因为真正融入了民间,那个曾在昆明和上海街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西南联大肄业生,最终完成了他真正的文学蝶变。
五
其实,从老舍到赵树理,再到汪曾祺、贾平凹等,我们能勾勒出一幅比较清晰的汲取民间文化、养成自己创作个性的现当代作家精神图谱。文化是有传承的,汪曾祺尊敬前辈老舍、赵树理,也欣赏晚辈贾平凹(称赞他“对西北的地方戏知道得很多”),雅和俗的程度不同,但乡土和民间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底色。
1989年,25岁的冯杰曾给汪曾祺写过两封信——求字和求序。蛰居豫北乡村的文学青年缘何结识了文坛名家?我们不得而知。从收在《汪曾祺全集(书信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汪曾祺的回信来看,字是写了的,却没写序,年近古稀的汪曾祺直言,他“已三四十年不读诗,偶于报刊看到时下新诗,瞠目不能别其高下。对于你的诗也一样,不知道属于几‘段’……”当年的文坛,还刮着现代主义的劲风,汪曾祺的话里是有话的。冯杰后来没在诗人的路上走下去,而是转向了散文、书画创作,并以故乡为根据地开辟出“北中原”这个独具标识的艺术园地,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汪曾祺当年回信的影响。
1989年的汪曾祺“瞠目”于文坛时风,而他所属意的是民族文化传统。也是在这一年,汪曾祺重写了两篇《聊斋》故事:《捕快张三》《同梦》。重写《聊斋》故事,是汪曾祺晚年最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这重写是从1987年开始的,那一年他重写了《瑞云》《蛐蛐》《黄英》《石清虚》四篇。其中后两篇完稿于美国。是年,汪曾祺受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邀请,赴美交流访问。在给妻子施松卿的一封越洋信中,汪曾祺说:“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以汪曾祺的性格,向来不自矜自夸的他,竟对自己的工作有如此评价,确能看出他对重写《聊斋》的重视。
1987年的这四篇小说是以《〈聊斋〉新义》为题集合发表的,汪曾祺在后记中说:“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这是尝试的第一批。”而在给妻子的那封信中,他还附了一篇写给出版社的《自序》,其中有云:
我年轻时曾受到过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我已经六十七岁了。我经历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从云层回到地面。我现在的文学主张是: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校中风气是推崇现代主义,他曾深受影响;而40年后当他真正到了西方,心心念念的却是“回到民族传统”。从现代主义回到现实主义,从西方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选择重写民间文学的集大成者《聊斋》,其中埋藏着他深刻的文化用意。
六
汪曾祺改写的《聊斋》故事中,关乎情爱者多。其中《画壁》一篇,他的改动并不大,只把原作的读书人朱孝廉换成了客商朱守素,故事整体未变:画壁前驻足,为垂髫天女所诱,入画中达成心愿,受金甲神人惊吓,出画外,见天女垂髫已变束发。这个人与妖、仙、鬼的故事,属于民间文化学者所谓“狐妻型故事”,但它却并不只是我们的民间才有。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詹姆森曾言,该型故事在琉球、北美、西伯利亚等地都有流传。他说:“它们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共性,反映了人类欲望与人类恐惧的本质。”([美]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共性证明了一种普遍性的价值,但让价值实现的却是特殊性。所以,汪曾祺才有理由重写《聊斋》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参以己意,使成新篇”。汪曾祺是多“情”之人,名作《受戒》《大淖记事》都是写爱情。文学中的爱情多来自现实中的爱而不得。“爱”是普遍性,“不得”却有特殊性。汪曾祺也好,冯杰也好,都写过因爱而生的悲剧,现实中的悲剧酿成了夜半枕前的痴梦,“料因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这些民间性情之响,来自最真实的民间生活,也传递出最真切、最质朴的情感与道德。
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只因山歌是更直接地出自民间,发于民心。民心即是人心和人性,是普遍性的。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也有显而易见的民间色彩,其中《往后靠的巫师》一篇写了一个有野心的教长求助巫师,却因吝啬而愿望成空的故事。这种违背诺言遭到惩罚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冯杰在他的另一本书《鲤鱼拐弯儿》(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中仿写了这个故事(《羊肉烩面——仿博尔赫斯》),他只是将故事发生地搬到了他老家的菜窖,教长变成了遇到人生难题的乡下青年,但德行和欲望的不匹配令其受惩罚的结局仍是博尔赫斯式的。
博尔赫斯笔下经常出现中国元素。1981年12月,博尔赫斯在家中受访时说:“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也想去中国……”然后他举起了手中一根手杖,“瞧,这就是证明!”那是一根来自中国的手杖。多年前,博尔赫斯在纽约唐人街购得。博尔赫斯甚至为它写过一首名为《漆手杖》的小诗:“我看着那根手杖,觉得它是那个筑起了长城、开创了一片神奇天地的无限古老的帝国的一部分。”
博尔赫斯始终没能到过这个神奇古老的国度,但詹姆森到过,且长久驻留过,他说:“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中国的民俗学者历年来做过很多工作,文学艺术领域对民间文化的汲取也绵延未绝,但时代的迅疾发展让一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文化的生成、存在方式和形式,都有别于以往。但这些长久以来都在很多人视线之外的文化珍宝,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生的,都值得我们仔细打捞、认真端详。
(作者:李勇,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文艺评论中心〔郑州大学〕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