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寒山吹笛唤春归‖唐雪元
寒山吹笛唤春归
唐雪元
寒潭渡鹤影,冷月葬孤魂。
故乡没有确切的概念,故乡就是曾经流过血汗并且让人生长的地方。我离开故土26年了,漂在西南。因从事媒体职业的缘故,采访过不少艺术家,听过、看过不少人的演奏。每当这时,我总是不由得想起那位英俊如竹、白衬衣蓝裤子、有着一双明眸如水但又有些忧郁眼神的小伙……

小伙,是我的表哥张白茹,一个女孩的名字。但我很喜欢,喜欢这名是因为喜欢他这人;喜欢他这人,是因为儿时在农村他演奏的笛曲最令我怀念、难忘,笛声悠长。
我家在湖南株洲市仙井乡(原叫鸿仙乡)的乐棠湾,表哥是我大姨的长子,家住醴陵市十亭乡炭眼冲。虽说是两个不同的市,可两地相邻,也就四五里地的距离。表哥所在的冲,当年属穷乡僻壤,有顺口溜:“有女不嫁炭眼冲,薄泥搅水到裤裆。”
村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种水稻为主,一年两季,然后就是西瓜、豆子和棉花等,村里人大都比较贫穷。我家所在的乐棠湾,就要好很多,相传本该是出皇帝的地方,只可惜被当朝的皇帝派顶级御用风水师给斩断了龙脉,泄了帝王之气。
记忆中,故乡的河流交错,每逢下雨,那是逮鱼摸虾的好时机,雨天能逮到好多鱼虾,自然也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村上我有一个当时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和邻居,她是朱江峰,她爸爸头脑活泛,打通了株洲一家机械工厂的门道,做一些“铜铁屑”生意,加上父母都会持家,自然比我家生活要好很多。每次和我一起玩和上学,她都会从家里带饼给我吃。那时的我,就像家中的小黄狗一到吃饭就守着我的样子。
村里没有什么文化娱乐,只有到了夏天,上村的男女老少人手一把竹椅、一把蒲扇,凑到喻家塘塘埂上吹风侃大山。下村的老少爷们便是聚在朱红朝爷爷招公家,听他泡一壶老叶子茶,眉飞色舞地讲《杨家将》或《说岳全传》,经常听得我们意犹未尽,直到月落星稀还不愿走,直到老人家装着拿大竹叉扫把追着撵,才悻悻离去。
这期间,最盼大表哥白茹来我家,他是我爸的徒弟,跟着学砌匠。我感觉他就是“学富五车”的那种秀才,肚子里的故事特别多,甚至比招公讲得还好。最难忘的是白茹哥的笛子演奏,什么《城南旧事》里的《送别》《九九艳阳天》《映山红》和电影《少林寺》插曲《牧羊女》等。人说音乐人生,这是在村庄里唯一能打动我心弦、使我充满神秘幻想的东西,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后来才知道,白茹哥只有到我家来,才可以这样放飞自己的小乐趣。
白茹哥的母亲、我的大姨,腿有残疾,他爸、我大姨爹倒是一表人才,长相帅气,可偏偏不顾家,好逸恶劳。白茹哥兄弟姊妹4人,他是老大。自小学习成绩特别好,一直是班上前几名,一门心思指望能上大学跳出农门。可大姨爹却不愿意供,加上那时农村人不重视读书,大人们往往都是要求孩子们能为生产队多干活,多挣点工分。这样一来,白茹哥只读了一个初二就辍学了,从此本应读书的年华,却承受着与年龄不相符的繁重劳动。有一次,生产队派他扛锄头拢红苕秧,白茹哥累了,就坐在田头看书,结果被生产队长发现后,就叫来大姨爹一阵辱骂,说他父子一个卵样,尽是偷奸耍滑之徒。大姨爹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不仅把他的书撕碎了,而且还把白茹哥狠狠地打了一顿,棍子打断了,还继续打。白茹哥就像一头拥有浑身力气但又无助的牛。后来的他,不再看书了,每天收工回家,傍晚就吹起他那也许唯一能发泄的笛子。
等我有了记事能力,发现我妈特别喜欢他,虽然那时的白茹哥下有两弟一妹,都叫她姨。但依我妈的话说,是因白茹哥长得最帅,一身白确良衬衣上身,下着一条蓝色的裤子,活脱脱一个“白马王子”。加之,他很有眼力劲和嘴甜,自然很是讨人欢喜。还有,白茹哥很上进,一心想重振他们那个破败的家,扶持弟妹们成才。母亲不止一次地流着泪告诉我说,白茹哥常对她讲:“姨,我发誓要振兴家门,我的爹妈是指望不上,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妈一样。但凡有一日我发达了,我一定接姨到我家好好孝敬!”
家庭贫穷和无知,确实能扼杀一个人的天才。白茹哥在我家帮忙干完农活,在歇息时或是下河洗完澡回家时,心情大好的他爱吹笛子,笛声悠扬。对于我来说,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穿透心灵的天籁之音,那是贫穷生活中精神世界的极品与精华。可是后来,大姨爹与白茹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火冒三丈的大姨爹硬是把白茹哥心爱的笛子用刀剁成两截。
冲突的起因是,白茹哥在跟我爹学砌匠出师后,用三年的打拼积攒了一些钱,准备拆老屋修一幢一厅两厢、外带厨房和猪舍的砖瓦房。想法是好的,当他提出让大姨爹也出点钱时,却被一口回绝,称自己没钱。气急之下,白茹哥忍不住说了他爹:“化生子爷,白活了一世人!”
化生子,湖南方言中,意为“败家子”的意思,多用于晚辈。现在白茹哥的这一句抢白,让大姨爹大为光火,很长一段时间父子反目如路人。
然而,房子终究还是修起来了。我妈直夸白茹哥“争了硬气”,多次教育我们哥姐仨要向他学习。
这期间,白茹哥邂逅了他唯一的一次爱情机会。
我们村一个姑娘的母女都看上了他,只因这家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女儿,故她家一不要嫁礼,二不嫌白茹哥穷,声称:爱的是人!
但这“爱的是人”也有条件,条件只有一个:招郎!
招郎者,即招上门女婿。在湖南农村,没有儿子的人家为延续家族,让男子出嫁,称为“招郎”。“招郎”入门后,女家长辈称其为子、为侄,忌称女婿、侄郎;同辈称兄道弟,忌称姐夫、妹夫;小辈称伯伯、叔叔,忌称姑爹。上门郎在女家享有财产支配权和继承权。
“招郎”有“两不辟宗”和“男从女姓”之分。“两不辟宗”又称“两边走”“半招郎”,即婚后男女双方家庭的生产和生活都要照顾,生下孩子第一个随母姓,第二个随父姓,余类推。“男从女性”即男子到女家后,生产、生活于女家,改随女姓,所生子女全随母姓。
这家母女找到我妈,托她“说媒”。我妈一听,乐不可支,马上同我白茹哥讲。原想他会乐意此事,且他年纪那会儿也二十五六了,是成家的年纪了。
不料,白茹哥不干,他气冲冲地对我妈嚷道:“姨,我自认为你最了解我最知我心意的,你竟然让我去招郎?对个堂客反而跟她姓,养个崽女也跟别个姓,如果这个样子,人还活个什么劲?如此窝囊一生,枉为七尺男子汉,要是咯样,我情愿打一世单身!”
我妈听后,一面不断叹气,一面又很欣慰,嗔笑道:“你呀,死咬卵,犟吧!今后真打了单身,莫怪我哈!”
我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话居然一语成谶。
来年春,白茹哥在帮我妈烧火做饭时,不经意间地讲道,说他晚上经常一个人默着家里的事睡不着觉,想着自己大了没有成亲,弟弟妹妹也跟着长大了,操心他们的前程,担心他们走了歪路……经常想着想着就头疼如裂。
白茹哥说这话时,我妈没上心,只是心疼他说:“我咯达崽哟,你们屋里就你是个清白人嘞!”
直到有一天,二表哥张洪堤骑着自行车火急火燎而来,进屋就哭:“姨嘞,我白哥哥不行哒,得了脑癌,哭得让我来喊你,说是要见你最后一面!”
我至今犹记,妈一闻讯,当即痛哭起来:“我苦命的崽哟……”一边往屋中陶瓮中掏出20个鸡蛋,一边让我抓米“诱鸡”关门逮了只大公鸡,再泣声吩咐我看好家。
说完,她坐上了二表哥的自行车,急匆匆而去。
第三天晌午,妈哭成泪人回来了,从她断断续续的哽咽述说中,才得知我所敬爱的白茹哥已永远地离去了——那一年,他才27岁。
听闻噩耗,我也哭了,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白茹哥了,也永远听不到他精彩的故事,看不到他演奏笛子了。自那以后,白茹哥那笛声,永远在脑海里回荡,忽远忽近,有时如清风细雨,有时似震耳欲聋。
又过了十年,我参军后探亲到了大姨妈家,酒过三巡,表姊妹们说起白茹哥往事,席间我执拗地提出:想去看看他!
一座荒山,满是荆棘,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之上,一个光秃秃、孤零零的坟堆兀然地立在那里,是那样说不出的凄凉和心酸。
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趴下身紧紧地拥抱住坟堆,大声地呼唤着白茹哥的名字,泪如雨下……
当天归来,我回到我们村子,首先绕着这曾经流过血汗的村子肃穆地走上一圈,然后坐在白茹哥当年给我吹奏笛子的石板上,追思和缅怀那逝去的幕幕往事。心想,假如白茹哥还活着,我一定送一支世界上最好的笛子给他。恍惚之间,耳畔萦绕起唐朝诗人李益的《春夜闻笛》——
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
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唐雪元(湖南株洲人,参军入川。国防时报社运营副总监兼媒体运营部主任,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创研部副部长,四川省文促会理事)
配图:方志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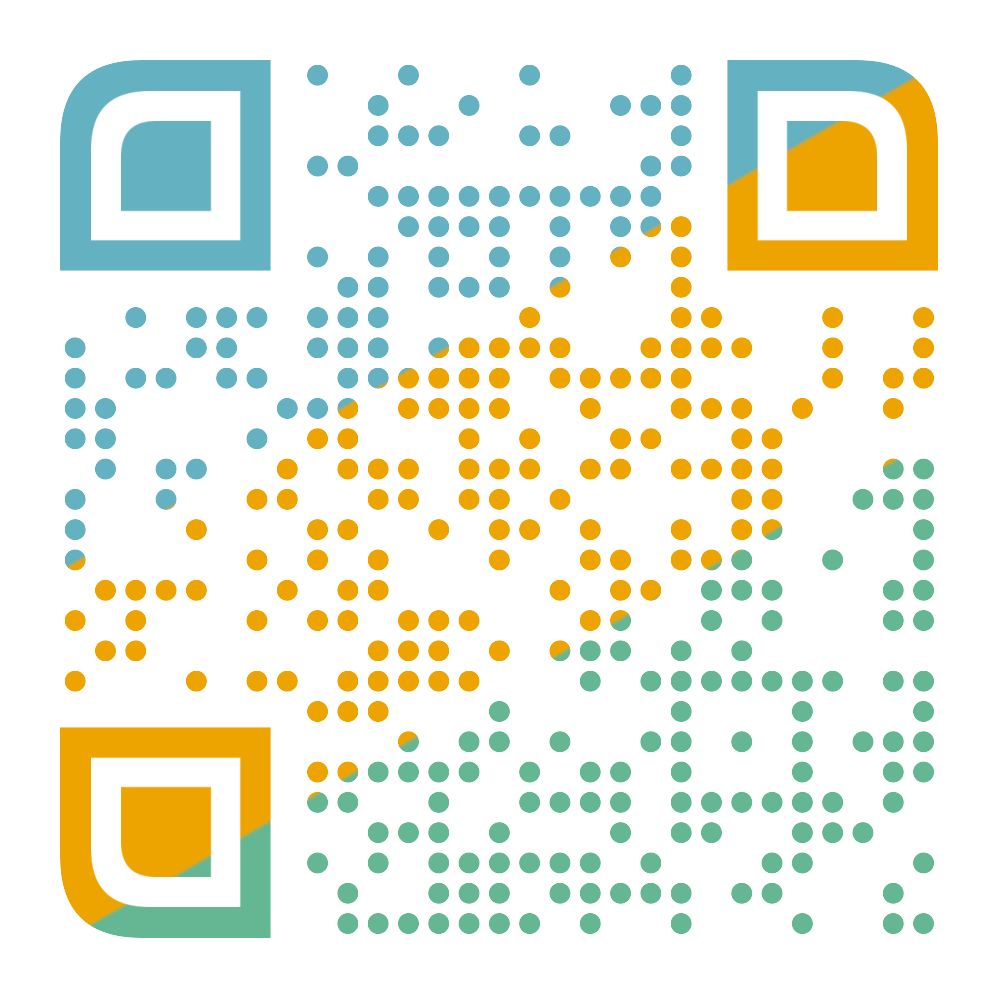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